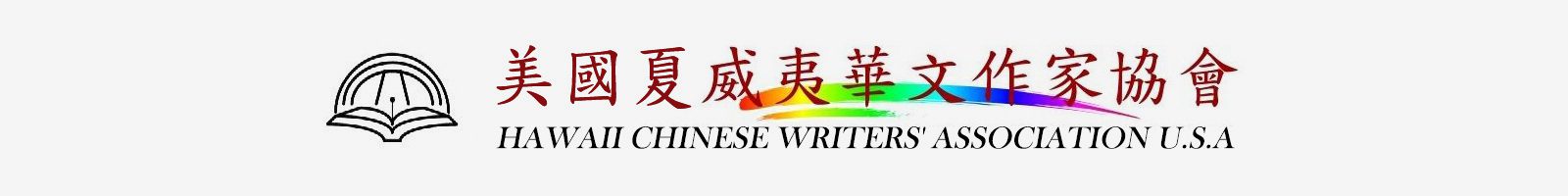魯迅的召喚與 韓中人文交流之未來
魯迅的召喚與 韓中人文交流之未來
朴宰雨
韓國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中國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李熙玉所長(以下簡稱「李」): 感謝您接受《成均中國觀察》的《PowerInterview》專訪。希望能通過本次採訪, 從人文學視角分析韓中關係, 並藉此機會向讀者介紹關於韓國學界的中國人文研究和中國的人文研究情況。 喜聞您在去年年底, 因在國際漢學研究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而被授予「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殊榮。 眾所周知, 「長江學者」被視為中國學術界的最高榮譽, 這一殊榮是對您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所取得成就的認可。
朴宰雨教授(以下簡稱「朴」): 我想這也許是中國學術界認可了我畢生的學術努力, 對此我很感激。大約在十餘年前就聽說過「長江學者」, 在人文學或中國文學領域,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斯坦福大學的王班、紐約大學的張旭東等知名華人學者獲得過此項殊榮。長江學者需要中國大學的推薦, 聽說要經過多達十幾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嚴格評審, 以及經過中國政府多輪審議才可以通過。嚴格的評審過程, 不僅評判學者本人的學術成就, 還包括對中國文化的熱愛理解程度是否深入。
李: 您應該是第一位被評選為「長江學者」的韓國學者?
朴: 我聽說理工科領域曾經有一位在美韓裔學者當選過。據我所知, 人文社會領域我是第一個。
與魯迅研究結緣

李: 再次祝賀您在學術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 並這一殊榮。您作為韓國代表性的魯迅研究學者, 創立了「東亞魯迅學」, 還擔任了國際魯迅研究會會長, 魯迅研究國際化的成果也得到了認可。在過去韓國的中國學界以及講台上忌諱現代文學研究的情況下, 您應該是介紹、研究和講授魯迅的第一代學者吧?
朴: 我想是我和魯迅的緣分引領我走向了研究中國文學之路。上大學的時候, 首爾大學的中文系課程以古典文學為主。上世紀70年代, 韓國處於維新體制時代, 這是一個學生運動和對政權批判的高潮時期。 大二時, 首爾大學文理學院學報《形成》的一名記者拜託我寫有關魯迅的文章, 其實, 我當時對魯迅了解的並不深入。所以, 我當時拜訪了成均館大學河正玉教授, 拿到了相關資料, 並聽取了建議。就這樣, 在首爾大學文理學院的《形成》上發表論文的機會成為了我以中國文學為業的命運之交。因為遇見了魯迅, 所以在知識和學術上得到了很多靈感。
李: 您在台灣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是關於《史記》和《漢書》文學的比較研究,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主題。這一研究也許成為了銜接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橋梁, 那從哪裡可以發現與魯迅研究相關的結合點呢?
朴: 我在台灣大學留學時, 那是一個不能公開談論魯迅的時期。當時,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是台灣大學的禁忌。但是, 我發現魯迅高度評價《史記》的文學價值。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所以, 我認為, 如果要學古典文學的話, 就必須學習《史記》, 因此我從文學角度寫了《史記》和《漢書》比較研究的論文。
李: 由此聽來, 您從大學時期就對魯迅很感興趣, 很早就認識到了魯迅研究的社會性。當時您在研究古典文學的同時, 似乎也在等待進行魯迅研究的機會。

朴: 是的。當時在台灣很難獲得關於魯迅的資料。上世紀80年代初至中期, 魯迅、巴金、茅盾等作家的盜版作品在台大正門前的小攤上開始出售。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 大陸當代作家的作品也逐漸開始出版。
李: 當時的韓國社會好像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在韓國也有一段時間, 現代文學研究被視為一門邊緣學科。我認為, 您在將制度圈外的學問引入到學術界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您認為當時魯迅被韓國學術界接受的意義是什麼呢?
朴: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 主要以台灣留學派為主, 也包括一些韓國本土派。在台灣留學派中, 當時正面評價魯迅文學的人寥寥無幾。我在寫本科論文的時候, 閱讀了丸山昇有關魯迅之文學與思想的日文版書籍, 對魯迅研究有了深入的理解, 產生了深刻共鳴。後來, 即使留學台灣, 我也下定決心有朝一日要研究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我想正是這十多年的求學生涯, 為我今後研究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打下了基礎。對此, 我往往聽到中國學者們對我這樣的學術經歷給予肯定的評價, 就是以中國古典文學為基礎再來研究現代文學, 可以說這是做到了堅實根基的學問。大學畢業論文, 我寫了大約四萬字關於魯迅的文章。80年代初期, 《文學東亞》季刊創立, 我的本科論文在那裡刊登。然而, 在台灣留學期間, 我無法繼續研究魯迅, 轉向了研究古典。
李: 當時,曾有擴展中國文學的研究範圍的嘗試,並且中國文學界也有所回應。
朴: 是這樣的。因為中國文學界被禁錮在保守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論上, 當時有思想的研究者非常壓抑。在這種情況下, 我策劃丸山昇撰寫的《魯迅—其文學與思想》的翻譯, 以《魯迅評傳》為名出版。還通過各種渠道, 魯迅也越來越被學界所熟知。特別重要的一個契機是, 1980年代, 李泳禧先生通過《魯迅與我》等類似文章, 撰寫有關本人的覺醒過程的故事時, 經常使用「吾師魯迅」這個詞。他活用魯迅的著作,在媒體撰寫了《知識分子與機會主義》、《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評論文章, 為提高知識界對魯迅力量的認知做出了貢獻。我認為, 他對於魯迅在韓國知識界被廣為人知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魯迅與韓國
李: 魯迅被評價為是一位文學家、評論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此看來,魯迅是一個複雜而備受爭議的人物。您長期致力於研究魯迅, 那您是如何評價魯迅呢?
朴: 早在解放前, 韓國知識界已經開始接觸到魯迅。當時讀魯迅的學者們, 主要把重點放在魯迅追求弱小民族的解放, 對弱者的同情, 被封建社會壓迫人們的批判和解放上面。韓國知識分子強烈期望朝鮮獨立, 因此, 從這一層面上, 他們似乎接受了魯迅。解放後, 正如李泳禧先生坦言的一樣, 閱讀從日本求得的竹內好的魯迅選集讓他醍醐灌頂,他從專制和法西斯主義, 軍閥集團的統治, 壓制人權, 社會的黑暗和腐敗等批判視角, 探討了魯迅文學和思想展現的意義。我認為80年代初中期, 研究中國文學的年輕學者探究魯迅與此也有關係。

李: 魯迅既是思想家, 又是文學家, 持續供給知識能量源泉, 可以說影響範圍是非常廣的。
朴: 是這樣的。所以也被稱為學術資源, 思想資源和文學資源。在這一點上, 我認為魯迅為做自我反思的生活和社會批判的眼光提供了重要資源。
李: 21世紀是一個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性加深制約而急速變化的時代。如果魯迅面臨這樣的巨變, 又會給現代社會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示呢?
朴: 正如剛才所談的, 將韓國社會接受魯迅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在日本侵略下, 給渴望獨立的韓國知識分子傳遞的啟示, 第二個是解放後, 給軍事獨裁下的知識分子傳遞的啟示。第三個是21世紀正在經歷多元化以及因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環境巨變的社會傳遞的信息。應中國學術界的邀請, 我調研了最近十年間韓國魯迅研究的走向, 在韓國有幾本通過發掘新資料研究韓國魯迅學的著書已經問世, 這體現了魯迅學發展新視角和努力的走向。另一個是魯迅傳記。過去, 魯迅的傳記大部分是由中日學者翻譯的, 但近來出現了以韓國學者的角度來撰寫魯迅傳記的趨勢。高美淑等學者參觀了魯迅曾經居住的地方, 為了發揮連接魯迅與青年的橋梁作用, 撰寫了魯迅傳記。像朴洪奎等學者還出版了名為《自由人魯迅》的書。像這樣, 在韓國, 專家學者正在努力從多個方面入了解魯迅的每一部作品。也有一種將魯迅的片段生活與自己的生活對比、作為自我反省的素材, 然後將魯迅應用到韓國情況的趨勢。最近李旭淵教授寫的《閱讀魯迅的夜晚-——閱讀我的時間》, 也是一本關於思考如何在韓國生活中理解魯迅, 思考如何將魯迅的思想與自我的內心聯繫起來的書。此外, 魯迅與家庭問題, 如果是魯迅, 將會怎麼做等等將魯迅的思想映射到自己的生活中, 劇變的社會環境中, 把他當作守護人文精神的靈感素材。
李: 魯迅是否有涉及到韓國和朝鮮的問題?
朴: 過去李泳禧先生曾指出為什麼魯迅從來沒有提到韓國。2005年, 我曾邀請李泳禧先生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當時李泳禧先生也向中國學者提出了相關問題。去年,一位中國學者發掘了關於韓國和魯迅關聯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資料, 可以看出魯迅並不是完全沒有提及。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當中梁啓超的發言, 他說:「朝鮮本是中國的藩屬國, 現在卻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令人痛恨」。魯迅曾指出梁啓超關於日本吞併朝鮮的言論「非常可怕」。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曾表示 「朝鮮應該獨立」。學者魏建功受到五四運動和魯迅的影響, 於1927年4月來到京城帝國大學擔任教師, 任教約一年半。中國的《語絲》雜誌連載了他撰寫的在朝鮮經歷的各種觀察和感受。其中, 有部分涉及中國對朝鮮的文化侵略傾向。梁啓超早期是改革主義者, 對韓國啟蒙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對申采浩先生也影響很大。但後來梁啓超逐漸轉向保守。當時甚至出現了想把在中國受到批判的封建文化出口到韓國的跡象。魏建功批判地指出了這一點。考慮到他把三國時期和渤海視為韓國的歷史, 魯迅雖然表面上對朝鮮沒有提及或提及不多,但可以看得出他對朝鮮還是掛在心裡的。魯迅雖然是日本留學派, 因為與日本知識分子關係密切, 所以並沒有說過積極捍衛朝鮮的獨立, 但我認為他對弱小民族的解放和獨立有基本的認識。
韓中人文交流的未來
李: 明年是韓中建交30周年。兩國建交以來, 雙邊關係取得重大發展, 但也經歷了曲折。這可以歸結是因為國家認同的差異, 而想要克服這些問題最重要的似乎是開展自下而上的人文交流與合作。如果人文交流與合作不能發揮很好的作用, 那麼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必定也有局限性。您長期在政府級別的中韓專家委員會擔任職務, 與中國一直保持着交流。您認為目前中韓文化交流處在怎樣的水平?
朴: 因為我主要關注學術、文學、文化領域, 所以我參加了大山文學財團委員會,並於2008年至2019年與中國作家協會和日本作家團一起成功舉辦了4次東亞文學論壇。有一次發生了以下情況, 2012年韓中日作家會議原定於北京舉行, 但因當時中日發生矛盾, 所以所有日程無限期推遲。當時主要是因為釣魚島的問題, 我也利用每次與中國作家協會見面的機會, 建議恢復東亞文學論壇和韓中日交流。之後, 2015年東亞文學論壇再次在中國舉辦。事實上, 相比多邊關係, 中方更喜歡雙邊關係, 但他們也希望通過接受三邊合作與交流來持續推進人文交流。
李: 中韓之間是否出現過磕磕絆絆的情況?
朴: 韓中兩國因部署薩德問題出現分歧, 雙邊關係也變得十分困難。但在與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幹部討論時, 我聽到中國領導幹部說越是這樣的時期, 就越應該繼續推進中韓文學和文化交流, 對此我非常感動。在存在某種程度的矛盾狀況下, 為解決這一問題, 我認為應該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作家之間的文化交流, 發揮作家的精神信使作用。雖然人文交流不能像表層政治那樣發揮表面上的力量, 但我認為如果民間的相互理解和關係積累起來,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消除政治上的分歧和障礙。
李: 韓國和中國的人文交流概念似乎各有不同。有評價認為, 如果韓中關係嘗試化學性地結合起來, 就要從更高的層面來討論人文的價值。您認為人文交流的方向應該怎麼走?
朴: 有觀點認為, 中韓人文交流停留在在機械性的交流層面。問題是中國和韓國的價值觀側重點不同。在中國最重視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 而在韓國則接受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的價值。在大框架下存在交叉的方向。如果想要尋找它們之間的共同點, 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軌跡中存在很多差異, 但我希望雙方努力把與共同認可的普世價值結合起來。當然, 在中國, 與普遍價值相比, 區分西方價值和中國價值的比率更高。但歸根結底, 既然不可能否認人類的普遍性那麼就需要努力使普世人文價值趨同和成熟。

李: 正如您所言, 韓國和中國有着數千年的文化根源, 如果從中發現的兩國共有的傳統價值適用於現代, 將會超越意識形態, 為進行高水平交流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礎。然而,我們如何發現這些傳統價值, 以及我們將哪一部分作為財富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朴: 是這樣的。例如, 有人評價魯迅是「東亞智慧的橋梁」。和我們一樣, 日本也翻譯了魯迅全集, 研究魯迅的學者也很多。也有知識分子想要發現韓中日之間的共同價值。如果能夠將傳統和現代的潮流很好地結合起來, 繼續推進多邊交流, 這將能成為東亞智慧的橋梁和重要的人文資源。
李: 在韓中討論的過程中, 雖然使用了「人文紐帶」這個詞, 但是如果把人文交流的層次分為交流、紐帶、共同體的話, 您認為韓中人文交流現在處於什麼水平?
朴: 韓中建交以來, 雖然雙邊交流發展迅猛, 但也有因文化、政治、經濟矛盾出現交流停滯, 甚至後退的情況。但是在人文方面, 我認為交流一直在進行, 相互理解也在不斷加深。如果看我們是否達到「紐帶」的水平, 我覺得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到了。但是各領域的「紐帶」能否跨越政治界限的問題, 現階段還難以定論。
李: 和其他領域相比, 人文交流的協調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正如您所言,大概可以概括為: 已經建立有多個可稱之為紐帶的平台, 並進行持續的、切身感受到的交流, 所以有必要以建交30周年為契機, 尋求質的變化。
中國如何重新成為更具魅力的國家?
李: 現就最近的問題聽一下您的建議。中國現在處於兩個國家形象之中。如果將具備將經濟和軍事實力等硬實力並投射到其他國家稱作能力國家, 而受到對方尊敬的國家稱為魅力國家, 從此觀點來看中國雖然是能力國家, 但似乎還不是魅力國家。中國領導人也正在討論如何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舉行了主題為「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集體學習活動, 強調中國應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和可敬的形象。您認為中國如果想要成為有魅力國家, 需要具體完善哪些部分?
朴: 說到魅力國家, 一般會提到西歐國家、北歐國家、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家。換而言之, 這些國家經濟實力雄厚, 社會福利得到保障, 文化、科學技術和藝術蓬勃發展, 自由生活得到高度保障, 所以他們好像已經接近魅力國家。但是仔細想來, 中國不是具有與此不同的魅力嗎?中國擁有廣闊壯美的自然景觀、精緻的人文景觀、多元的文化等眾多極具魅力的資源。但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中國的魅力局限於古典部分。因此, 如果我們完善現代部分, 中國將樹立一個有魅力的國家形象。我希望能夠在與中國民間自由交流的同時, 發現和共享人文和現代價值。為此, 我希望進一步擴大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如果可以創造一個人們可以開誠布公交流的環境, 外國人會發現中國人更多的魅力。
李: 研究公共外交的學者說, 「不要給糖衣, 應該給蘋果」。我認為, 比起只是單方面地展現中國美好的宣傳, 展現中國缺陷的開放性也許會更有助於交流。
朴: 魯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像阿Q一樣的人物,毫無保留地展現了中國歷史具有的傳統缺點和奴性等。我覺得認可並努力克服這些缺點的努力本身就是美的, 很有魅力的。
李: 最近, 中國學者經常被要求坦誠地說出中國所欠缺的是什麼部分, 您長期關注中國並與中國一直保持交流, 您看來, 中國在哪些方面需要有所改進?
朴: 作為專業是漢學的人, 我真誠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具有國際魅力的國家。但局限性在於, 與韓國不同,歐洲和美國等國將孔子學院視為單方面的文化宣傳工具。我認為, 比起人為的運作, 如果能找到溝通真心的平台, 那麼會在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對各種價值以包容、開放的姿態對待, 用真誠態度與外國人交流的話, 那麼中國可以發展成為更有魅力的國家。
文化矛盾的反思與解決
李: 在韓國, 中國的國家形象未得到改善。在韓中高層政治穩定發展的同時, 民間的負面認識卻進一步深化。特別是, 未來韓中關係的主力軍MZ一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煽風點火」的作用。每當如泡菜之爭、韓服之爭、防彈少年團問題和韓國戰爭等問題觸及兩國人民的情感時, 被隱藏着的令人不安的歷史回憶很容易被喚起。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您認為有什麼解決方法?
朴: 可以從政府間和民間兩個角度來思考。在韓國, 民間的自主權非常大, 而中國的大體上具有根據官方指導確定方向的特徵。特別是, 如果中國官方以韓國文化與朝鮮族文化具有本質共性為由, 將其視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化, 即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那麼韓國可能會難以接受。考慮到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朝鮮族與韓國及朝鮮, 蒙古族與蒙古共和國, 還有傣族與泰國等, 存在一定的關係。如果把所有屬於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化都稱為本國的文化是不合理的。雖然政府對此沒有明文規定, 但會誤導中國民眾朝鮮族文化與韓國及北韓文化是相同的這會對中國文化產生誤解。在這方面, 我認為如果有政府的適切引導, 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李: 這應該是起因於文化起源主義的問題吧?
朴: 是的, 比如中國官方誤解的部分當中有一個是江陵端午祭。中國學者也評價江陵端午祭與中國端午節是屬於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因為2005年前後是韓流風行之時, 普遍認為韓國擔心中國竊取文化, 所以韓國搶奪端午節並將江陵端午祭申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此後不久, 中國端午節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像韓國阿里郎擴大地解釋為既是朝鮮族的阿里郎,又是中國的阿里郎, 來傷害韓國國民情緒的問題, 如果中國政府以學術研究為基礎, 在民間進行適當引導的話, 很有可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並更容易的去解決矛盾。再比如,說韓國人主張孔子是韓國人, 間島則是韓國領土等說法, 但事實上, 韓國主流學界根本沒有此類主張。經常是極少數人的謬誤傳播為整個韓國人的認知都是這樣。所以, 我曾經提議建立一個可化解相互誤解的機構, 雖然目前已經有韓中人文論壇, 但還沒有一個可以集中管理這個論壇的機構。我希望當新冠疫情結束後兩國之間能夠建立常設管理機構並解決由誤解引起的各種問題。
李: 我認為這些問題是由於中華豐富的文化強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近代國家的框架中所造成的。正如您所說, 如果以歷史起源主義來看待問題, 恐怕就沒有答案了。我認為中國和韓國在東亞共同文化認同的背景下, 應樹立更具包容性的歷史觀和認知, 這對促進中國和韓國之間的關係發展至關重要。目前,韓國的中國學界文史哲基礎非常薄弱。在中國研究的大框架下, 韓國的中國學研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並應該朝着什麼方向發展?
朴: 中國的中國學研究因為是國學, 因此在數據整理和考證等方面具有優勢。但, 我認為現代層面來講, 高水平重新詮釋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曾與一位德國著名的漢學家對話, 他強調了現代重新詮釋的重要性, 同時評價了許多國家的中國學研究。在中國學研究領域, 日本是傳統強國, 美國和歐洲在新的批判性解釋上做得很好。我聽說韓國也被評價為中國學研究領域的新興國家。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們對中國學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 也有一些人自我評價稱我們傾向於過度汲取中國大陸或台灣的研究成果。過去台灣留學派, 以及韓中建交後大陸留學派的研究具有些模仿轉述性質,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國內派研究者則過度地拘泥於「韓國主體性」的視角因此。首先需要有一個從世界普遍的角度出發, 對任何問題都能進行反思和反省的基本姿態。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才能進一步深入思考我們中國學研究的不足之處。
李: 感謝您今天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們的採訪。最後, 請您對《成均中國觀察》的讀者說幾句話。
朴: 我覺得和而不同、易地思之、求同存異的態度不僅在人際關係中, 而且在國際關係中也都十分重要。我希望中國和韓國的讀者在這種精神的基礎上建立相互的關係。和而不同是指具有自主意識, 不隨聲附和, 而相互和諧。我認為《成均中國觀察》以「異地思之」的態度, 既向讀者很好地展示了韓國的視角, 又充分考慮到了中國立場。雖然中國和韓國之間存在些矛盾點, 但可貴的是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尋找和諧共處的方向。希望成均中國研究所以後也繼續發掘高水平、恰合時宜的主題, 為加強韓中人文交流與合作做出貢獻。謝謝!
(劉珂 譯/安波 校)
朴宰雨 韓國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中國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首爾大學中文系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 博士
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部 榮譽教授
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韓國》韓方主編
國際魯迅研究會 會長
世界漢學研究會(澳門)理事長
歷任 韓中文化論壇 組織委員長
韓中專家共同研究委員會 社會文化組 組長
首爾國際文學論壇、韓中日東亞文學論壇 組織委員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會長
韓國中語中文學會 會長